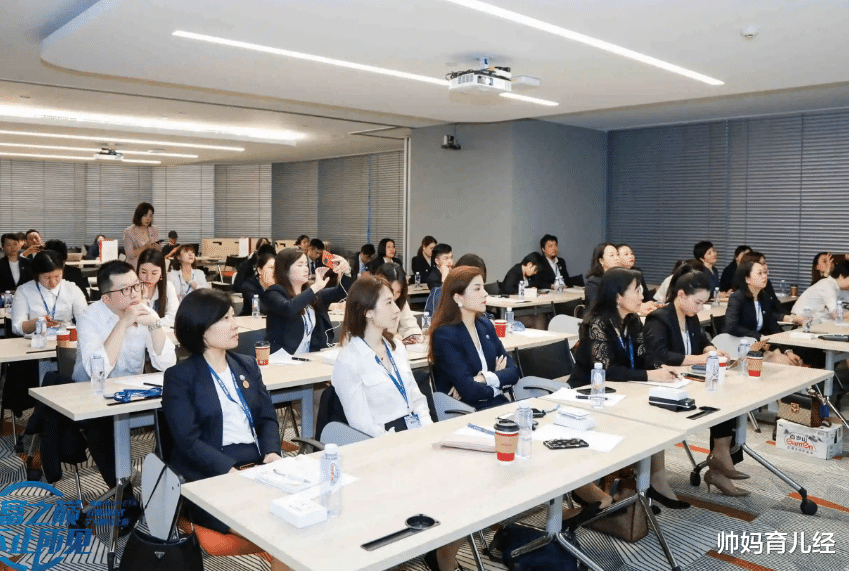陆胤(章静绘)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陆胤主要从事晚清文学及学术思想史研究,近年尤其关注近代中国教育转型与读写文化变迁的关系。清季新学堂骤兴,以“国文”为名的新式文学教育应运而生。国文一科既是新教育模式的产物,又涵纳了传统蒙学和古文词章之学,负有培养读写技能与脉延国族文化的双重使命。在他今年出版的新书《国文的创生:清季文学教育与知识衍变》中,陆胤从思想理念、制度设计、教材编刊、教法变革等多个维度考掘了清末国文教育创生的过程,更试图以此为入口,探索近代知识形成的普遍机制。在接受《上海书评》专访时,陆胤指出:作为现代语文教育的源头,清季新生的国文教育不仅是近代国族文化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更以屈折的方式延续了中国固有的“文教”传统。重访“国文”理念与国文课程的发生现场,实有可能在“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的既定路线之外,触及中国文学古今之变的一些更为深细的脉络。
《国文的创生:清季文学教育与知识衍变》,陆胤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6月版,544页,99.00元您在书中详细讨论了清末新学制的筹划和国文教科书的编纂,在此过程中,文学教育从依托科举的“教士之学”转化为追求普及的“国民教育”,最主要的变化体现在哪些方面?
陆胤:从“教士之学”到“国民教育”的变化,不单发生在文学教育领域,更是清末从理念到制度上重新确立一整套新学体制的结果。只不过文学教育在这个过程中有它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古代教育不是铁板一块,各个时代各具特点,但各个时代的教育大概都要从识字作文起步,科举考试的“以文取士”更巩固了诗文在教学中的地位。包括识字、辨训、读作古诗文在内,广义上的文学教育充当了古典教化的基础,自然会成为近代文教变革的一个主要对象。加之甲午战争以后,趋新之士热议文字、文体与国势的关系,逐渐萌生“国文”“国语”的意识,更使得有关本国文字、文学的课程成为新教育风潮中首当其冲、备受关注的领域。
就文学教育而言,实现你所说从“教士”到“教国民”的转化,最大的“坎”在哪里?在《国文的创生》的绪论中,我归纳了近代国文教育区别于传统词章教学的三个方面,也就是制度化、专科化、普及化。下面分别来说一下:
制度化就是强调国文课程背后有一套“通国一律”的学制。1904年1月,清廷颁布癸卯学制,确立“中国文辞”一科,又按学程细分为“中国文字”“中国文理”“中国文学”三门,通称“国文”。国文课程贯穿了从初等小学直到大学的各级普通、专门、师范、实业学堂。在理想状态下,同一学程所用教科书、教学法应大体相近,不再延续传统社会按地域、阶层、行业乃至家族门风而“读书风气各别”的状态。
新学制下的国文一科还要横向处理好跟其他学科的关系,既要有所区别,又要互相照应,以共同致力于某一学程的总体教学目标。这就与明清时代专注于日用杂字或举业之需的蒙学形成了根本的区别,跟传统书院分散考课的模式也有所不同。在学制创立之初,人们心目中的“国文”是一门与修身、格致、外语、体操各科并立的“新学”,国文教科书也一度被视为“洋书”。
图一:癸卯学制稿本中“国文”一科在各科之间的位置与官方强力推行的制度化过程相对,专科化则造成了“国文”的另一个比较柔软的侧面。国文非但是一门课程,也是一个可以逐级深入、自成体系的学科门类。国文教育不限于启蒙阶段的读写训练,在“普通学”的应用之上,也有超功利的“专门学”“美术学”属性。作为“专门学”的国文科吸收了文学史、语法学、修辞学、美学等外来知识体系,同时也涵纳了古典词章之学的资源,在新学堂一隅延续了一部分传统的教学模式。清末乃至民国时期,一些科举出身的旧文人托庇于中高等学校的国文专科,国文课堂成了“国学”的保留地。本来作为新名词的“国文”,也逐渐沦为保守的代名词。这种由新入旧的理念变化,跟国文专科化过程中树立的“学科壁垒”不无关系。
最后是普及化。讲到文学教育的普及,就要涉及整个教学理念的变动了。正如你所说,中国传统教化主要是“教士”,虽有“有教无类”的理想,但受制于教育资源和国家能力,实际上仍侧重于拔取少数统治精英,未必像后人想象得那般平等开放。晚清洋务时期开创方言(外语)、武备、水师、工艺等专门学堂,最初仍遵循这种“教士”的思路,与科举“正途”并行不悖。直到甲午战败以后,系统改创教学体制、建立一整套涵盖全体国民的学校体系,才逐渐成为朝野的共识。
十九世纪国民教育模式从西欧到日本不断扩展,随之而来的近代民族国家的成功,给晚清士人带来很大冲击。他们意识到教育的意义原来不仅是选拔统治精英,更要“造国民”——使士、农、工、商每个人都能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之中。而要让全体国民接受教育并理解政治,语言、文字、文章是主要媒介。包括提高识字率、推广浅近文体、提升政治文本的理解和再生产能力等目标在内,文学教育的普及成了当务之急。新生的国文教育至少在理想上排除了传统蒙学在“经塾”和“蒙塾”之间的阶级区分,覆盖了不同地域、性别(有“女子国文教科书”)、族群(有“满蒙汉三文合璧国文教科书”)。当然,必须意识到的是,读写能力的普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清末发轫期的国文教育只是提出了目标,其完成则有待于整个新学体制向内地和基层的渗透。
国文教育的制度化、专科化、普及化的达成,还有赖于一种全新的知识载体——“教科书”。教本、教材是古已有之的东西,但“教科书”(Textbook)却是清末从外国导入的一套新体制。清末教科书正是在文学教育领域首先发端,从戊戌前后新体蒙学读本的创制,到学制确立时期国文教科书的编定,背后有一条连贯的脉络。(参见拙著第二章)
不同于传统学塾使用的“三、百、千、千”或“四书五经”,近代教科书传达了限时完成的课程规划、由浅入深的教学进度、界限分明的学科内容,以及在同一教学空间中感受到的知识共鸣。尽管教科书的设计往往与教学现实脱节,好学生也从来不会自限于教科书,但教科书塑造近代国人集体意识的作用实不容低估。从经书到教科书,知识权威的源头不再是圣人的垂训,而是出版社的编纂和学部、教育部的审定。最近网上关于“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讹为“斯人也”的纷争,正可说明教科书的权威:网友或媒体求证文本的是非,首先想到的依据,竟然不是石经或宋版的《孟子》,而是各个版本的语文教科书!
图二:作为国文教科书前身的新体蒙学读本您认为“在张之洞等学制主导者的话语中,‘国文’服从于维系国族共同体的宏大目标”。清末以来的“国文”强调书写文字和书面表达,似乎仍是一种不够彻底的教育策略,能否谈一下国文教育与“五四”前后更为人们熟悉的“国语统一”和“文学革命”运动的关系是怎样的?与“国语运动”相比,国文教育的收效如何?
陆胤:“国语运动”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学革命”,可以说是整个“五四新文学”发生的内核,学界有太过丰富的研究,我不想多谈。但这两大运动的效应不断外溢,早已成为近现代文学史乃至文化史研究的一种支配性话语。从一百年前胡适发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起,有关晚清文学的讨论就一直被“国语运动”的后设叙事笼罩,几乎让我们忘却了“国语”之外还有“国文”!除了国语运动史和文学革命史的既定路线,与近代新教育同步发生的“国文”理念与国文学科,有没有可能为我们考察文学、文体的古今之变打开一些新的视域?这是我结撰《国文的创生》这本书的一个出发点。
“国文”和“国语”这两个词,作为学科、课程的名称,都是清末从日本导入的新名词。在明治日本教育界追求“言文一致”的主流氛围中,“国文”“国语”其实是一体两面,“国文”就是“国语”的书面形态。但在近代中国,“国文”和“国语”却分化成了两类知识。清末“国文”从一开始就不限于“以文字代一国之语言”,而是沿袭了来自传统蒙学、“小学”、文章学的诸多内容。与一心要跟“汉文”剥离的日本“国文”不同的是,中国“文”的传统是自生的,并不需要依附于“语”来获得主体性。作为国文学科的一个补充,癸卯学制附设了“官话”课程,却迟迟没有为“国语”正名。以统一语言为目标的国语教育,在清末时期大体仍处在民间“运动”的阶段。民元以后,形势陡转,国语运动在体制内迅速取得声势。1920年教育部颁令国民学校改“国文科”为“国语科”,国语一科不仅宣告成立,更有吞并国文的势头。
前面讲过,清季新学堂中的国文课程本来是一门“新学”。其思想起源与甲午以后涌现的切音字方案、白话文运动(两者后来都被纳入广义的“国语运动”)并无二致,都是为了回应国势衰微带来的语文危机意识。但“运动”腾播于舆论,可以无比激烈;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性活动,则必须考虑社会习俗和接受心态。清末教育家多能注意到当时“语”“文”分离的实际:公牍、书札、报刊上主流的文体仍是文言,文言在方言多歧的情况下比官话更为通行,也更适应新学堂所要传输的科学内容和新名词。国文教育的实用化要求,势必不容许教育者去高攀尚未达成的“国语”,而忽略日用文言的现实。
基于这一层考虑,同时也经过了文、白之间的试验,新体蒙学读本和国文教科书的编者最终达成了使用“浅近文言”的共识。他们所说的“浅近文言”,是介于“应用的古文”和白话文之间的中间状态:仍取古文通行的法度,却尽量简化古典词章家讲究的句法、词藻、事类,努力吸收新语汇和适应学童心理的新题材(如科学故事、名人传记和动物寓言)。晚清时代,传教士曾根据西洋修辞学将中文文体分为三类,提出介于“深文理”与“白话”之间的“浅文理”。戊戌以后,梁启超倡导容纳新语汇和欧西文思的“新文体”,其实深受明治日本“汉文训读体”文章的影响。有别于切音字、白话文启蒙的通俗路线,国文教科书采用“浅近文言”,与同时期传教士的“浅文理”或新学界的“新文体”理念可以说是桴鼓相应,都是在传统文章延长线上探索一种文体改良的现实方案。
图三:1905-1908年前后福建兴化府官办中学堂的读书场景,HarrisonSacketElliott摄影由初学阶段的“浅近文言”拾级而上,国文课程在中学以上更趋向从唐宋八大家到清代桐城派的“古文”传统。我在书中指出,古文能力在晚清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既可凭借体段笔法通向科场时文、经世策论,又有助于形成报章议论需要的文字功底,甚至还可以充当翻译西学的媒介。就此而言,古文并非“死文学”,也未必像张之洞最初设想的那样,一定能充当抵拒新名词和“外国文体”的屏障。较之形式感更强也更为封闭的诗赋、骈文,“雅洁”的古文其实更容易对接新思想和新语汇。清代桐城古文家多任教于书院,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而桐城派影响的铺开,却是在晚清以后。清末新式学校和教育管理机构中多有吴汝纶、吴闿生、高步瀛、姚永朴、唐文治等古文家活跃的身影,《古文辞类篹》《古文词略》《经史百家杂钞》等桐城系选本作为中学国文教科书的典范,也为学生在《古文观止》《论说文范》等“俗选”之外指点了作文的“向上一路”。
从更长的时段来看,古文家追求“雅洁”“义法”,正是古文通行于各时代的流量密码。史家吕思勉曾指出,相对于诗赋骈文等特殊文类,古文淘汰了一时代一地方的特色语,有使古人与今人接近之效,可称之为“时间上之官话”。如果说“国语统一”有助于国族空间共同体的建成,那么以古文为进境的“国文”则是国族时间共同体的纽带。语言瞬息变化,文字历古不磨。片面强调当下语言的普及性,也有可能割裂古、今之间由文字文章搭建的沟通渠道。这正是张之洞等学制主导者特意强调“国文……即间有时势变迁,不尽适用者,亦必存而传之,断不肯听其澌灭”背后的深心。
至于你所问的,国文教育与国语运动“收效”的比较,窃以为二者或许不能简单比量。因为“国文”和“国语”各自构成了近代中国读写文化工程的两个侧面,又分别代表了缓进折衷和急进革命两种风格,各有功效,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相互成就的关系。“五四”文学革命带来的现代白话文,是我们能切实感受到的工具;国文教育传承的文化肌理,则往往是日用不知的习惯。清末新学中人虽大多向往“言文一致”的语文前景,但当时较为现实的主张,却是文语并行、雅俗不妨,也就是刘师培所说的“一修俗语,以启瀹齐民;一用古文,以保存国学”——“国语”和“国文”两条腿走路。教科书所用的“浅近文言”,正可充当沟通二者的中间文体。
这种带有功能区分的双层语文结构(diglossia)适应了教育实际,却未必符合近代以来“语言民族主义”和“声音中心主义”的标准。文语并行策略在民国以后遭到激烈批判,认为其割裂了同属一国的“士大夫”与“小百姓”,被视为晚清文学变革“不彻底性”的表现。然而,一国语文的同质化又焉有止境?不旋踵而“新文学”又因不接地气而遭到“大众语”的挑战,最终只能通向一片黄茅白苇。后起的国语运动要用“语”来收编“文”,本是基于语言先于文字、文章描写语言的理论预设。但假如口头语言和书写文字本来就有不同起源、不同功能,“言”和“文”自古就不一致呢?这些问题,清末章太炎在《文学说例》《文学论略》等论文中有非常深刻的论述。国文教育着眼于应用文章,看起来不如“国语运动”激烈彻底,也缺乏“文学革命”的纯文学品位,“国语”取代“国文”更被渲染为既成事实。但在教学现实中,“五四”以后,中学以上国文科在文言文之外对接了语体文的新传统,直到1949年才改称为“语文”。“语文”是“国语”加上“国文”,“文”的传统并没有消逝。
您在全书一开始就提到,“清季国文教育从一开始就负有培养读写技能和脉延国族文化的双重使命”,但新学制下的国文课程又“带有强烈的功利导向”,这一导向是否意味着“国文的创生”从一开始就处于教育目标的各种纠结之中?
陆胤:是的,徘徊于“文化与技能”“情怀与功利”“美术与实用”之间,国文教育看上去有点纠结,甚至相互冲突。但细究起来,每一个目标的提出都有自己的脉络;有些看上去冲突的地方,背后有相通的理路;不同目标之间,有时候也可以相互配合。这又得返回到清末教育变革的思想史背景来谈。
以实用技能和科学方法为旨归的近代教育体系,在西方也是相当晚近的产物。十九世纪,欧洲公立学校的古典语文课程开始衰落,科学教育逐渐占据主导。以斯宾塞《肄业要览》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教育论和传教士散布的“格致”之学,在晚清新学家的圈子中颇有市场。甲午以后,趋新者对于中国传统教育的一大指控就是“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国文虽是一个新学科,但教学内容的一大部分来自“历古相传之书籍”。所以新式文学教育从一开始就面临着自证“有用”的压力。
比如1898年首次出版的《马氏文通》一书,如今已被尊为中国人自著语法书的始祖;但当初马建忠撰作此书,却有学术创造之外更为宏大的愿景。马氏原是要为学童提供一套文章速成法,来缩短文学教育年限,使他们能把原先消磨在文字上的时间花到更为“有用”的科学上面。差不多与《马氏文通》同时,采用近代教科书体例的蒙学读本也开始涌现。这些新体读本正是今日语文教科书的源头,但取之与现今课本对照,有一点差异非常明显:清末的国文读本在初学阶段采用大量科学素材,往往兼有各科综合读本的性质。当时新学堂里的国文教习若是不懂科学,也有可能被学生看不起。国文课最初作为“科学津梁”的功利侧面,跟今天人们印象中偏向人文性的语文课有很大不同。
图四:充斥科学内容的新体蒙学读本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人接受新知识的图景相当复杂,科学话语散布的同时,国家学说和近代国族意识也以日本为中介涌入国内。在此过程中,更孕育了“保存国粹”的运动。有关文字、文法、文体的教学,也借此“东风”而被抬升到了维系国家统一和国民爱国心的高度。除了政治话语的加持,“国”与“文”密切关联的背后,还有一层学术传统的支撑。众所周知,清代经史考据大兴,作为考据基础的“小学”(指音韵、文字、训诂之学)赢得了一切学问基础的地位。道咸以降,考据学声势稍减,却并不妨碍从“小学”出发的学术理念凝固为张之洞等学制主导者的常识。
跟传统书院中的“词章”一门相比,清末新学制下“文学”的内涵要复杂得多:传统“小学”和语法学、修辞学、文学史等“洋学问”同时被纳入,原本处在词章中心的诗赋却遭遇边缘化,更不用提在官定学制中被严格管制的小说戏曲了。按照奏定章程的规划,大学堂“中国文学门”的形态其实更接近西洋古典“语文学”(philology),而非晚近以诗歌、小说、戏剧为框架的纯文学(belles-lettres)。沿袭乾嘉诸儒“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路径,癸卯学制还在中小学“读经讲经”和“中国文学”两科之间设置了隐含的配合关系。这一安排一公布就遭到了新学界的猛烈抨击。新派人士更愿意把国文与读经对立起来,凸显国文课作为新学工具的形象。然而,在国粹派与趋新派的分歧背后,其实有着共通的理路,也就是把“文”当成通向某个外在目标(无论是科学还是国粹)的手段,这些各异的外在目标又服务于共同的国家目标。
清末国文教育确实包含了新、旧互相冲突两面,但两者分布在“普通学”和“专门学”的不同阶段,未必会在现实中形成冲突。当时留存的一些学务调查报告,为我们揭示了不同学程间迥异的评判标准:小学国文课常考察是否采用教科书和新式教授法,中高等国文则相对更注重文风、文统的传承。即便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式教科书,到中学阶段也会回到古文选本体例,强调记诵和评点。教学现场的情况则更为复杂:一些名义上的小学堂还在采用私塾教法和教材(如《古文观止》之类);另一些中学堂则相当激进,直接采用移译自域外的修辞学教科书或教师自编的文法讲义。在师范没有普及的年代,国文师资来源复杂。是探索新国文,还是温习旧词章?取决于学堂风气和国文教员的个人趣味,有时候会非常随机。
图五:清末各种不同层次的文学教科书在第八章中,您描述了当时在国文教育中“记诵”与“讲授”之间的争论,对传统蒙学教学方式的争议直到今天还在持续。您认为,国文教育在学制、教本、教法等各个层面,都呈现了“制度与习俗”之间的张力。您能以记诵与讲授之争来具体说明吗?
陆胤:请允许我先澄清一下拙著第八章提出的“记诵与讲授之争”。我所强调的,并非“记诵”与“讲授”二者的对立本身,而是建构起这组对立的过程。从教育事实来讲,无论古今中外,本来都不存在“记诵”和“讲授”的冲突,学习过程中记性和悟性两者从来都是相互为用的。中国古人强调记诵工夫,但并不排斥“讲书”;儿童入学记诵到一定程度,就要给他“开讲”。欧洲近代以后注重实验和理解,却也不可能完全排斥记忆。
如果说有什么根本上的“古今之变”,可能还在于教室空间和教学秩序的组织。就像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大家所熟知的景象:学塾里每个人都在大声念自己的书,塾师也陶醉在自己所念文章的调子里面,并没有新式学校中那种井然的秩序、齐声的朗读、划一的课程。换言之,传统教学空间里头并不存在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共同体”,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路线上展开各自的“读书功程”。非但记诵是这样,讲解也是个别、分散的。从个别讲读到集体教学,这跟清末民初引进“国文”“国语”的同质化追求是完全同步的。
那么,在这个从个别分散到整齐划一的同质化过程中,为什么“记诵与讲授”的对立会被提出来?我想至少有传统内在变化和外来观念刺激两个因素。从传统教化的内部来看,宋元以降“记诵之学”确实上了一个新台阶。一方面是科举竞争越来越“卷”,在考试指挥棒驱使下,塾师的首要任务就是督促温背,很多时候顾不及仔细讲书。另一方面,两宋理学兴起,朱熹等理学家喜欢总结“读书法”,他们发现记诵这件事也有修身功能,可以“收放心”。慢慢地,跟理学家素来注重的“静坐”“调息”一样,记诵经书也成了一门存养的工夫,所读内容的理解和领悟反而不是最重要的了。“读书千遍,其义自见”,理解是记诵到家以后自然会达成的效果。近世学塾教法注重记诵,既有表面上人人皆知的应试考量,也有潜意识中习焉不察的修身考量。元儒程端礼所编《读书分年日程》在明清两代非常流行,就是结合了这两方面考量,设计了一套通过反复记诵塑造士大夫人格的流程,计日程功,积年成才,为记诵的普及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操程序。
然而,时至晚清,当传教士、外交官这些“陌生人”闯入的时候,学塾中的记诵场面却给他们带来很大刺激。外来者未必能看到记诵背后的知识再生产动机,更来不及体会理学家凭借记诵“维持此心”的深意。他们只是对最直观的诵读声音大为惊诧。尽管西洋古代和中世纪教学同样置重诵读,但近代科学兴起后,古典语文教养遭遇功利主义教育观的挑战,理解和实验方法日益流行。近代来华的这批新教传教士,已是身处欧洲文教“古今之变”的洗礼之后。他们强调记性与悟性、诵读与默读的对立,进而将死记硬背、大声吼叫、夏楚相加等要素凝注为中国式教学的刻板印象。
十九世纪后半期的西文读物中不乏描绘中国学塾的画像或照片,不难发现这些图像多是遵循一定程式的描摹或摆拍:昏暗的房间中散坐着严厉的塾师和苦恼的学生,而且总有一个学生背对着塾师在“背书”(图六、图七)。传教士的观点感染了梁启超等趋新士人,并在彼辈“常带情感”的笔锋下进一步被夸大,“中学记诵”和“西学讲授”之间俨然形成不可调和的对峙之势。短短数年之间,以“讲授”取代“记诵”迅速成为整个新学界的共识,并很快凝结在了新学制的条文之中。
图七:1880-1890年代DavidKnoxGriffith摄于香港的“背书”;同一空间在变换布置后,也曾用来拍摄女学生做女工的场面。可知并非教学场景的实录,而是基于刻板印象的摆拍。清末趋新之士口中的“记诵”常是中国学问整体落后、野蛮的象征;与之相对的各种西法“讲授”,则包含了集体教学、分段教授、问答启发以及黑板、粉笔、课桌椅、教科书等教具在内的一切进步要素。这组对立本身就是一种理念的建构。基于新学精英理念与外来学制模版匆忙厘定的新学制,自然难免要跟数百年“土地所生习”的教化习俗有所出入。清末新学堂体制面临着新旧、官民、城乡之间的多重博弈,牵扯到广泛的社会利益和经济纠纷,引发了一系列闹学、毁学事件。“记诵”与“讲授”的对立化,也可看作新学堂推广过程中诸多摩擦的一种表现。
对于晚清读书人而言,反复温背和出声诵读正是一种教化习俗。清代古文家的“因声求气”论,曾国藩等人格典范的诵读实践,都为记诵读法提供了更为切近的依据。在新学导入之初,甚至连《新民丛报》这样的报章也可以成为反复吟咏的对象。当时许多新学堂依然延用旧教法,国文一科则是“记诵”与“讲授”拉锯的主战场。直到民国时期,中小学国文甚至国语课堂上仍不乏传唱诵读调的例证,更不用说高等以上国文专科中流行的“黄调”(黄侃的吟调)或“唐调”(唐文治得自吴汝纶的吟调)了。但制度设计在适应现状的同时,也确实在慢慢改变习俗,或逐渐消解旧教法的一些功能。比如在外来演讲术、朗诵术和音乐教育引导下,民国时代的诗文吟咏就有越来越偏向美学感受的趋势;由于科举的废止、理学的式微,诵读服务于记忆和修身的传统功能则在不断弱化。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旧学塾的绝迹,课堂集体讲授成为新的教学习惯;即便是大学中文系学生,也开始对传统诵读感到陌生甚至惊异了。到此,这场绵延一甲子的“读书革命”才算真正收束。
近年来不乏有识之士重新提倡吟诵,作为个人修养或课外的兴趣爱好,我当然非常乐于鼓吹。我自己在北大讲“大学国文”课,也会播放唐文治、赵元任、钱仲联、朱东润诸老的诵读录音,借以告诉学生,怎样才是品读古典诗文的正确方法。但要说到宣传推广乃至纳入基础教育的课程要求,我个人还是有点保留。毕竟支撑记诵教法的整套文化制度——大到科举制,小到吟诵专用的地方读书音(不同于方言口谈,是绅士阶级读书时专用的一种地方性“绅谈”)——在过去一百二十多年从日常语言到国民教育各个领域的同质化过程中,已经全然被改换了。这也正是近代以降国文课、国语课、语文课区别于古典词章传习的一个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