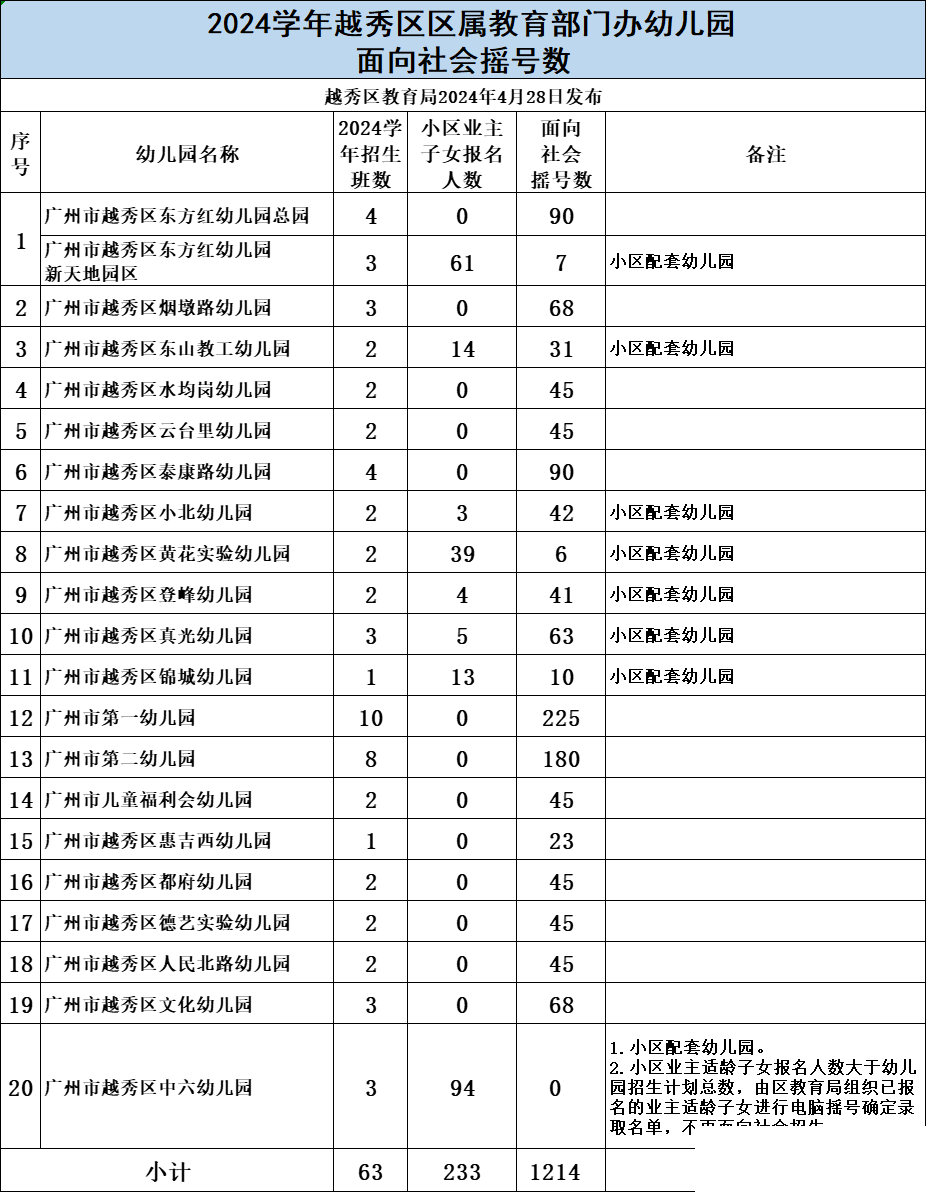“我们有很多培训,但防欺凌是第一次。”班主任牛晓雨看了眼台上的幻灯片说道。
“可不是最近这些事闹的,教委动不动就找上门。”有老师小声议论,“上面都有文件要求了。”
4月12日下午1时,随着近百位老师和校长陆续落座,一场针对教师的防欺凌培训即将开场。主讲人是该市的律师陈亮。
六年来,陈亮多次进入校园开展防欺凌教育。他发现,欺凌事件在学校并非个例,但问题迟迟没有得到解决。
今年以来,几起恶性事件的发生,让“校园欺凌”再度成为焦点。
3月25日,教育部组织开展“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周”主题活动,其中就包含校园暴力专题教育。4月底,教育部将实施学生欺凌防治行动,对所有中小学校“起底式”大排查。
从2016年起,全国已开展过多轮防治校园欺凌的行动。
但在多位老师眼中,目前学校的反欺凌工作,仍是一种“短暂、被动的落实”。
老师究竟能做什么,该做什么?当舆论的风暴停歇,他们真正的难题等待解答。
待解的难题
六年前,陈亮第一次接触到“校园欺凌”。
他接到6岁儿子的来电。对面不停地啜泣,“爸,你来接我!”陈亮急了,他赶紧问发生了什么,孩子不回答,只说要立刻回家。
陈亮和妻子决定联系孩子的老师。他们了解到,孩子参加校园滑雪的冬令营,在同学里面年纪最小,别的同学都喊他“小屁孩”,带的零食和游戏机从来不和他分享。
当时在陈亮眼里,这些“不就是小事吗”,他给儿子买了巧克力、玩具,却没法安抚孩子的情绪。后来,在妻子的询问下,孩子说,两个男生把滑冰的靴子扔在了他的枕头上。
陈亮的妻子变了脸色,“这是校园欺凌。”她反复和陈亮说,这类现象是必须介入的。
两人立刻找孩子的老师沟通。不久后,老师组织了全班同学集合,厉声说道:“你们不能这么做。如果再发生类似的事,我会通知家长把你们领回去。”这一番话,给了陈亮很大的安全感。
陈亮回想,那些孩子只是小小的恶意,但没有老师及时的教育,时间一长,很可能出现更严重的欺凌行为。
每年的普法日,陈亮会受到该市中小学的邀请,给学生们做法治讲座。2018年起,他决定讲讲校园欺凌。
经常有女孩在讲座后偷偷找过来,“我被欺负了,不知道和谁说。”有德育主任领着男孩走到陈亮面前,“班里的同学孤立他,让他很低沉。”......
陈亮发现,原来有许多孩子,掩藏着被欺凌的心事。
2020年,华中师范大学曾对全国六省1万余名中小学生进行调查,得出校园欺凌的发生率为32.4%。意味着每10位学生中就有3人经历过欺凌。
多年来,陈亮看见防治欺凌的行动一轮接一轮开展,法律规定越来越多,但欺凌事件仍在不时发生。
为何防治难以奏效?陈亮在寻找答案。
另一头,老师们同样心存困惑。
校长刘超坦言,从去年11月,山西大同曝出未成年人被同宿舍学生凌辱两年之久,到今年3月,河北邯郸发生疑似校园欺凌的杀人事件,一次次舆情下,反欺凌已经成了学校必须要做的事。直到现在,大家对“什么是校园欺凌?”还是没有概念。
雷竞技raybet即时竞技平台 班主任周晴曾是校园欺凌的受害者。舆论的升温让她想起了往事。
初一下半年,周晴从乡镇转学到县城。她刚站上讲台,听到有人喊:“农村娃子!”课堂里爆发出大笑。同学们对她指指点点,从头发点评到鞋子,说着“好土”。
周晴僵在讲台上,带着求助的眼神看向班主任。对方听到笑声后没说话,抬头看了一眼,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从那天起,嘲笑、辱骂等冷暴力在全班范围内出现,持续了三年。
很多次她埋怨,如果当初老师能够及时制止,或许欺凌就不会发生。
直到周晴进入学校工作,她开始意识到,老师面对欺凌,其实有很多难处。每当身边有欺凌现象,她总想做些什么,却又无从下手。
“校长不断强调要注意欺凌,每学期都有主题班会。”周晴说。但她和多位老师表示,目前还没有专门的培训说到,面对欺凌,老师究竟该怎么做?
他们正等待解答。
隐蔽
培训一开场,刘超在台上发问,“欺凌到底是没发生,还是没发现?”
底下的老师陷入沉默。有人小声嘟囔,其实出了“大事”,也就是严重的肢体冲突,班主任都会管的。但在校园里,更常见的是隐形欺凌。
华中师范大学的调查指出,在中西部130多所中小学的一万名学生中,言语欺凌的发生率是17.4%,高于身体欺凌的12.7%。关系欺凌的发生率为10.5%。
这些欺凌往往难以被察觉。
语文老师时斌在带教时遇到过一个女孩。在时斌眼里,她一直都是“别人家的孩子”,和同学相处融洽。去年10月,女孩突然和时斌说,“我不想学了。”原本活泼的她变得消沉,上课总在走神。
时斌记得,家长发现后很生气,指责她不好好学习。没过几天,女孩直接把自己关在家里面不出来,不和所有人接触。
期间时斌和女孩的家长聊过几次天。去年底,她的家长开始反省,是不是自己对孩子太严格?一直以来,孩子都不愿意上学、社交。
直到今年3月,女孩才和父母袒露,之前在班级里被其他女生孤立。别人都不和她讲话,她开始厌恨学校和同学。
在此之前,时斌和女孩的班主任从没发现过这些事,女孩也没有向他们求助。
“告诉老师是件很丢脸的事。”周晴回忆,初中时没有向老师诉说,是因为和长辈之间有天然的隔阂,也是出于自尊。她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被欺负了,也不想被同学说向老师打小报告。“更怕老师告诉家长后,他们反而指责我。”一位受到欺凌的学生说,家长会骂,“天天不好好学习,搞些有的没的。”
对此,老师能否主动侦察?
陈亮说道,对于学生变化,很多老师不够敏感。当孩子的行为、想法、性格跟往常完全不同,比如他们开始抗拒学校,产生厌学心理,身上不时出现伤口,或是以前很活泼,突然变得沉默。“可以在课后花5分钟、10分钟和他们谈谈,可能会发现欺凌的苗头。”
周晴最早在班级安插了“眼线”。吃饭、下课和午休期间,她都会待在教室里观察学生。结果令她沮丧,“学生私下发生的事,根本不会摆在明面上让老师知道。”
部分学校在每个楼层设置了心愿信箱,让孩子把被欺负的情况写下来。“没有人署名。”一位校长苦笑,孩子们生怕影响到自己的形象,也怕被同学报复。老师要长期调查,才能找到信件的主人。
牛晓雨想了个办法:她在校园欺凌的调查问卷上做了记号。匿名的世界里,孩子的诚实超出她的想象。好几次她顺着记号的线索,反复试探下,找到了班级里实施语言欺凌的学生。
但多位老师坦承,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备不完的课,开不完的会,写不完的报告和材料,管理学生的工作只限于课上40分钟和极少的空闲时间。”一位老师说。
何以界定
比起发现,如何界定令刘超更加头疼,“到底是欺凌,还是打闹?”
他害怕家长“小题大做”。“现在家长都知道什么是校园欺凌,出现什么事都往这上面靠。”好几次,家长找到学校,说自己孩子被校园欺凌。该校一位领导干部记得,有家长报了警,老师和派出所一调查,发现是孩子之间的小摩擦,或是双方相互打架。老师只得耐心和家长解释缘由,一些家长投诉到教育局、市民热线,教委立刻就找学校询问。
陈亮解释,界定欺凌得看两方面:欺凌者有主观上的恶意。“行为不是一时兴起的,他们明知道会给对方带来伤害,还要这么做”。欺凌行为客观上造成了损害结果的发生,无论是身体、心理还是财产损害。
其中最难的,是恶意的判断。
陈亮曾找过实施言语欺凌的同学,对方和老师辩称“我这是开玩笑,我们闹着玩的。”当时老师点点头,并没有当回事看待。
陈亮指出,实际上玩笑和嘲笑区别很大。玩笑是双方互相逗趣,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嘲笑以羞辱对方为目的,权力和地位并不平等。如果对方反击“我不喜欢这样,请你立刻停止”,嘲笑还在继续,就属于欺凌。
但心理是门复杂的学问。判断标准很难捕捉孩子内心深处的感受。
心理学教授孙莹是一所中学的德育副校长,曾为受欺凌的孩子做过帮扶。她看到,这些孩子的性格普遍胆小、自卑。她得营造出一个绝对安全和信任的环境,去接纳孩子的负面情绪,他们才愿意说出真实的想法。
他们说,自己怀有负罪感,“我肯定是哪里做错了。”“我是有问题的,别人才会欺负我。”
为了得到群体的认可,甚至为了融入欺凌他们的人,这些被欺凌的孩子宁愿去承受伤害,不愿拒绝和反抗。孙莹又去问了他们的老师,结果到了老师眼里,“这些人不是天天玩在一起吗?怎么可能是霸凌和被霸凌的关系?”
欺凌者反而觉得委屈。孙莹收到过家长反馈,孩子在学校里看不惯同学,经常打骂对方。家长觉得孩子的欺凌行为没有问题。“是被欺负的学生自己犯了错。”他们说,孩子是在纠正和反击。
“尽管一些恶意看起来很小,每个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有所不同。”陈亮记得,那位被嘲笑的孩子回家后,晚上头疼睡不着觉,梦里都在喊几位欺凌者的名字。之后接近两年的时间里,家长辞去工作,带着他辗转各大医院心理门诊。
陈亮叹息,当初或许是老师一时疏忽,但欺凌带来的心理伤害是持续性的。
初中毕业后,周晴从一个有点骄傲,爱出风头的小女孩,变得沉默少言。一旦别人的目光集中在身上,她会出汗、发抖,仿佛回到了报到那天,脑海里全是嘲笑的脸。“真想把自己藏起来。”她说。
丑事
一旦确定为欺凌,该怎么办?
多位老师指出,目前处置欺凌,仍然没有可以参考的细则。
他们坦承,自己没有很大的惩戒权,难以掌握教育的尺度。
“家校关系是脆弱的。”教师于星龙感到无奈。他批评了实施欺凌行为的孩子,孩子回家后告状,家长马上找于星龙维权。校长一直和于星龙强调,不要和家长闹矛盾,处理好家长的情绪。
每学期,于星龙学校的老师都有社会评价的考核项目,由家长进行打分,所有老师的打分决定着学校的分数。一旦分低了,教育局会找到校长问责,校长就会找到低分的老师批评。
后来,每当于星龙遇到不是很严重的欺凌现象,只找孩子和他们的家长聊聊天,让双方知道问题的存在。“哪怕是口头批评,我也隐晦地说,生怕说重了给孩子带来伤害。”
“老师也要保护自己。”陈亮强调,在处理欺凌事件时老师要注意“留痕”:记录好事件的基本信息、工作流程、处置结果,每次处理事件时都要询问学生是否认可,让他进行签字。这些材料可以作为事后和家长沟通的书面证据。
但处置还面临更大的难题:在家校眼里,欺凌是件需要遮羞的“丑事”。
时斌回忆,被欺凌女孩的家长曾找到校长质问。按照时斌的说法,校长很为难,没有实质性的暴力行为,要处理实施欺凌的学生并不现实。为了不让事情继续发酵,校长对女孩的家长说,对不起,我没有办法处理。但你们有其他要求都可以满足,要什么时候来上学,想换个班级,都是可以的,只要不把事情闹大。
孙莹观察到,家长同样心存顾虑,不愿公开表达。一位女生被同学扇了耳光,抢走零花钱。家长起初的反应是,我要去学校讨个说法。
没过多久,她和孙莹说,自己很矛盾。“孩子毕竟还在学校读书,除非发生恶性事件,不然冷处理吧。”“这群实施欺凌的孩子还在学校,处罚了他们,孩子以后怎么跟同学交往?”
不久后,家长决定让孩子转校,换一个新的环境。时斌记得,女孩的父母也选择了妥协。他们对时斌说,马上要中考了,不可能去找对方麻烦,算我们倒霉。
而根据孙莹的追踪,一些转校后的被欺凌者,又再次遇到了相似的欺凌。
2016年《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曾指出,各地要建立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事件及时报告制度,一旦发现学生遭受欺凌和暴力,学校和家长要及时相互通知,对严重的欺凌和暴力事件,要向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报告。
但孙莹感受到,平日校方给她反映的欺凌事件很少,到了恶性、极端的程度她才会知道,校方的反应经常是,“你们太敏感了,这就是小孩闹一闹、玩一玩”。
陈亮在学校调研时,校方反复叮嘱,教育行业很敏感,不能出现地区和学校的名字。调查能得到的样本和信息是有限的。
对此老师们直指,惩戒是缺位的。
“大事化小、息事宁人。”孙莹苦笑,这是许多欺凌事件的结局。
教育的反思
于星龙回忆,每当有舆情出现,学校就会格外重视欺凌的防治,但一般只持续两三个月。“校园欺凌早就老生常态了,每次都是治标不治本。”
在短暂的风暴后,学校能否建立起应对欺凌的长效方案?
培训结束时,一位中学校长找到陈亮,“我们很想重视防欺凌工作,但毕竟经验有限。”
在陈亮看来,应该调动更多第三方力量参与到校园欺凌的防治中,可以是校外的心理学专家、法律从业者、教育工作者等,具有跨学科的知识背景。
根据陈亮的观察,尽管学校有法治副校长的岗位,但很多法官、检察官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深入了解校园里的情况,最后往往“挂名了事”。因此不仅仅要强调社会责任,也需要通过制度设计、考核评优等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的积极性。
到底算不算欺凌,需要有一个具有公信力的判断。在上海、广东等省市,许多中小学设置了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由校长牵头负责,成员涵盖社区工作者、家长代表、校外专家等,能对相关事件进行调查评估,进行监测和报告。
更重要的,是教育系统内部的反思。
周晴记得,曾经比起欺凌行为本身,她更在意的,其实是成年人对于欺凌的态度。
时斌至今仍在后悔。当初发现女孩的异常时,他没有好好找女孩聊过,还心急质问她,“你怎么变得和那些差生一样?”很长时间里,女孩的班主任和家长都在指责,“孩子实在是太矫情了”。
时斌发现,现在老师们都在努力和学生做朋友,一起打游戏、做体育活动,“我们看似距离很近,实际上却很少有心灵的交流。”
如今,他尝试去了解每一位学生的性格特点,观察他们的情绪变化。“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你遇到什么烦恼了吗?”碰到情绪低落的孩子,时斌总会想,也许多问一句,就会有变化的发生。
雷竞技raybet即时竞技平台 时的周晴,第一次产生了当老师的想法。她遇到的班主任,愿意聆听她的心结,试图去安慰、鼓励她前行。周晴想和他一样,要做一个“很好的老师”。
渐渐地,她对过去的控诉,变成了对教师角色的思考。
现在相比于成绩,周晴更关心学生的心理和德行。听到班上有非议同学的声音,她害怕这些想法升级成更大的恶意,会公开纠正其中的错误。她看到,不是全部的学生都会转变,但只要一部分人受到触动,恶意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少。
她也意识到,老师对学生的影响会在潜移默化中发生。
周晴坦承,老师的偏爱有时无法避免,但她不想在学生面前明显表现出倾向性。换位思考,学生觉得“我被老师讨厌了”是种很难受的感觉,也容易让班上对这位同学产生无意识的排斥。
“已经过去了。”周晴笑道,一些伤痛无法消失。但她仍然相信,教育拥有改变的力量。
(文中受访者除陈亮外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