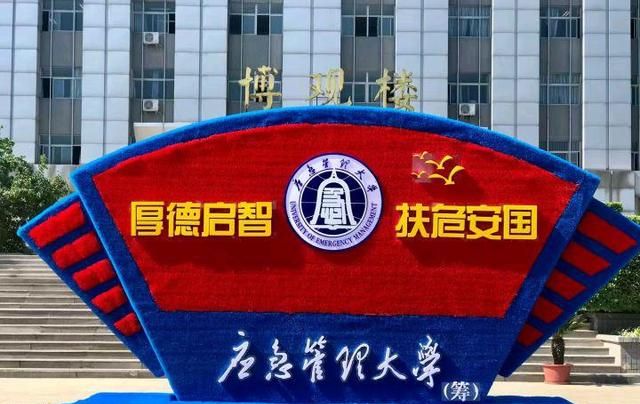不久前,即将30岁的我在家人催促下答应去相亲,母亲兴奋地动员全家一起物色,最后将一名资料无可挑剔的男士介绍给我。
这位男士不仅出身优渥,外形出众,而且是本硕都在美国念完的“海归”。接触过后,我还发现他是个颇具风度和爱心的人,但凡遇到有人乞讨,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打开钱包。
一切都进展得非常顺利,直到我们发生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争执。
那天,我们偶然谈到“该不该感谢人生中的逆境和苦难”这个话题。对此,他的想法是:“人生的每一个瞬间当然都是美好而值得感谢的,哪怕是痛苦的时刻也是如此。”
我忍不住小声反驳:“这种过于理想化的说法,等到真正遭遇病痛折磨,亲人离世,或是因为缺钱而不得不放弃理想的时候,应该不会有人还说得出口。”
没想到他愣了片刻,接着爽朗地笑起来:“我告诉你,假如一个人真的放弃理想,那绝不会是因为缺钱,因为能用钱买到的东西,都没有任何真正的价值,对吧?”
我没有回答,而是看着他32岁依然天真的面容和清澈的眼睛,不由得想起了26岁的陶远舟,想起他悲哀失落的表情,常年干燥起皮的脸颊和嘴角,还有中年人似的浑身抹不去的疲惫。
我在想,若他也听见这番话,是会因羡慕而痛苦,因不甘而愤怒,还是会无奈地苦笑起来,像往常一样,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
1、背着单反的年轻人
我和陶远舟初次见面,是在2015年春天。那时我毕业不久,在社区上班,工作清闲,因此想给自己报一个韩语班,没想到报名时无意中说起曾在日本留学的事,被正好苦于招人的校长问愿不愿意来兼职教日语,不仅能抵扣韩语的学费,还能再赚点零花钱,我于是爽快地答应下来。
在一次韩语课上,我们正学到一半,教室门忽然被小心地推开,一个斜挎牛仔帆布包的朴素青年轻手轻脚地走进来。韩语老师问他是不是新生,他先是猛点了几下头,抬头看见黑板上的韩语,脸上顿时露出窘迫的表情,对着我们认认真真鞠了一躬:“不好意思走错了。”然后飞快地跑出教室。
半小时后,韩语课结束,我走向隔壁教室准备开始自己的初次日语教学,进门便立刻注意到,端坐在课桌前的其中一人,正是刚才走错教室的青年——大学二年级的陶远舟。
由于年龄差距并不大,我们很快成朋友,经常在课后一起出去玩,而几乎每次出门,他都将一台看起来沉甸甸的单反相机挂在胸前,走走拍拍,仿佛对一切充满好奇,从不感到厌倦。我知道他是工科的学生,有一次故意问他:“这么喜欢拍照,怎么没读摄影专业?”
陶远舟叹了口气说:“我当然是想学,但是艺考太花钱,家里那会儿挺穷的,父母就强制我选了个看上去好找工作的专业。”
听他说“家庭困难”,我着实有些意外,因为在我看来,他此时的消费水平在大学生里至少是中等偏上的。原来他也有过吃苦的日子。
“不过没关系,现在条件好多了。”陶远舟忽然露出开朗灿烂的笑容:“等我学好了日语,就去日本读摄影专业的研究生。”他的语气轻快,却充满坚决的意志。
后来的几年里,我曾反复回想起那天他的样子:年轻,快乐,自由,对未来充满期待,有一双从未见过阴云的,干净清透的眼睛。
作为朋友,我从陶远舟的讲述中得知了他早年的经历,也近距离旁观了他这些年的遭遇。
因此,我比任何人都明白,他再也无法做回那个无忧无虑的青年。
2、他的摄影梦与留学梦
陶远舟的摄影梦起始于16岁。
那年,正在读高二的陶远舟从父亲手里接过了人生中第一台手机——使用塞班系统的老式诺基亚功能机。彼时他对摄影并无了解,只是随手点选了拍照功能,然后跑到阳台上,对着楼下灰色狭窄的老街和阳光里绿得发亮的香樟树拍下了第一张照片。
仅200万像素的摄像头下,世界并不如现实那样清晰明艳,但看着手机屏幕上被框住的一方天地,一种如同狩猎者捕捉到猎物般的快意使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并从此为之深深着迷。
直到雷竞技raybet即时竞技平台 毕业前,陶远舟用这台诺基亚,一共拍下了近四万张照片。
他雷竞技raybet即时竞技平台 时期拍下的旧照片之一
由于偏科严重,二十多分的英语严重拖累了高考总成绩,陶远舟复读了一年,最终也只考上了离家不远的一所三本院校。在这座四线小城边缘的“末流本科”里,迟到和旷课是教学楼里的日常,而烟酒和游戏则是男生宿舍的日常。
乌烟瘴气的环境里,原本因高考失利而痛苦,一心想靠大学的发奋学习在毕业后出人头地的陶远舟反而成为了异类。
一天晚上,年轻的辅导员前来查看宿舍情况,到了陶远舟的寝室,被几个室友拉着坐下嗑瓜子聊天。为了不显得太孤僻,原本戴着降噪耳机背单词的陶远舟也不得不围了过去,发现他们正在聊就业的话题。
“就我那点工资,还不如隔壁烟草公司的门卫!”辅导员发出感叹,接着又说,“倒是你们专业有个学生,前两年回老家创业,听说赚了不少钱,养了两百多头猪呢!”
在室友的嬉笑声中,陶远舟感到心里有一些东西正在熄灭和下沉。他想起,从事树苗采购的父亲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他说:“假如毕业后找不到好工作,你就回家,跟我一起种种树,养养鱼,好好过完这辈子。”
想到自己很可能度过庸庸碌碌的大学生活,甚至就这么度过一生,沮丧和焦躁将陶远舟压得无法动弹。
将他从这种灰暗的心态中拯救出来的,是偶然看见的一条题为“日元汇率下跌,正是留学好时机”的新闻。
留学这件事,原本因为太贵而从未被认真考虑,但他在搜索后发现,去日本需要的留学保证金原来并没有想象中多,生活费也远比欧美便宜,如此一算,以家里的收入水平倒勉强供得起,而且考日本的学校,还可以不用学最头疼的英语……陶远舟越想越激动,认为这正是为自己量身定做的最佳选项。
2015年春天,我与他因为日语学习这一契机而相识。那年暑假,即将进大三的陶远舟还前往深圳,在一家知名外语学校交了两万学费,进行了每天八小时的日语强化学习。
晚上,他住在深圳打工的姐姐租的城中村小房间里,用拆下来的老旧木门当床板,铺在几张平行摆放的凳子上勉强入睡。如此坚持了两个多月,他的日语水平果然有了显著的提升。
3、不堪一击的普通家庭
2016年3月的一个晚上,和往常一样埋首于复习资料的陶远舟接到父亲的电话,那头父亲的声音格外慌张,让他“做好心理准备”后,沉默了许久才说:“是你妈出了问题。”
前一天夜里,陶远舟的母亲突然感到腹痛,急送医院后,医生用手在腹部一摸,立刻觉察出问题,并安排做了B超,结果一个13公分的肿瘤赫然现形,紧接着化验完癌症指标,当日就确诊了肝癌。
陶远舟的父母都生在农村,文化水平不高,但为人踏实勤劳,辛苦打拼多年,终于在一座三线城市买房落了户。然而在陶远舟上雷竞技raybet即时竞技平台 时,父亲跟人合伙做运输生意亏了二十多万,生活又陷入困顿,父母不得不将他一个人丢在家里,共同南下打工。用了近七年时间,到2016年时,他们终于还清了债,还攒下小几十万积蓄。
就在家里的经济情况刚刚好转时,这个意外降临了。
几个月后,陶远舟迎来了大学阶段最后一个暑假,但他没有按计划再去深圳学日语,而是回到老家,独自照料生病的母亲。
在陶远舟的印象中,母亲是个“最普通的中国劳动妇女”,善良老实,勤快节俭,不爱穿红戴绿,但也讲究干净整齐,细软的长发在中年时剪成了更显精神的短发,笑起来和气真诚。现在她虽然得了癌,除了体力显著下降,外表却与从前并没有很大差别,这让陶远舟经常幻想,会不会像电视剧里那样,其实只是一次误诊,最后还是皆大欢喜的结局。
在老家生活,陶远舟每天早上七点准时起床,做好母亲的早饭后,一路小跑去菜场,买好当天的食材。每顿饭通常有一两道青菜和一碗汤,骨头汤和鱼汤换着做,这已经是二十几年没下过厨的陶远舟厨艺的极限。
晚餐过后,他会去附近学校的操场跑五公里,然后在洗漱后尽早入睡,因为医生曾提过给母亲做肝移植手术的方案,最适合的供肝人,自然是年轻健康的陶远舟。为此,他必须锻炼身体,并为了护肝而杜绝熬夜。
大四下学期,陶远舟因实习而第二次前往深圳。为了在日本系统地学习摄影前先积累一些拍摄经验,他选择了一份淘宝服装拍摄助理的工作,一直实习到毕业答辩前夕。拍摄过程中常常需要弯腰,而且一拍就是一整天,陶远舟很快就有了腰伤,为了减轻疼痛,他不得不带上具有些许支撑作用的束腰带。
2017年6月,陶远舟大学毕业,随即开始四处奔波,对照中介列出的留学材料清单,一项一项地准备着复杂的申请材料,打算于10月赴日。
然而此时,陶母由于病情恶化,家乡医疗水平又十分有限,不得不住转入广州一家医院接受治疗。于是,没有参加工作的陶远舟接替了父亲,开始在医院全天候陪护母亲。
新医院为陶远舟的母亲选用了“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法”——将一种放射性极强的粒子植入肿瘤内,通过持续不断的辐射去破坏肿瘤组织。
为了保护周围的人不受辐射影响,陶远舟的母亲不得不24小时穿着沉重闷热的铅防护服。有一次在CT室,当陶母应医生的要求脱衣接受检测时,刚刚掀起防护服一角,医院的放射性监测仪就立刻响起了骇人的警报。与此同时,周围所有病人和医护人员都像一群惊惶的兔子似的,开始以她为中心向四面逃窜。
“那个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简直就像个妖怪。”后来,陶远舟的母亲回想起当天的事,忍不住向身旁的儿子感慨。而陶远舟只能长久地沉默,一句安慰的话也说不出。
从被确诊开始,陶母就保持着每月一次的频率进行介入手术,每次的费用在四万上下,虽然术后能靠医保拿回一万多,但停工照顾她的陶父没了收入,住院期间还要承担远高于平时的食宿和交通等开销,在十余次手术过后,陶远舟家的积蓄由从前的小几十万迅速缩减为不到六万。父亲便向陶远舟提出了推迟赴日的要求。
窘迫的现实前,陶远舟不得不将留学计划推到次年4月,并决定在剩下的大半年里再次前往深圳工作,尽量多攒些钱。可新工作才刚有着落,陶远舟就从父亲那里得知了母亲的病情进一步恶化的消息。医生还说,肿瘤已在陶母体内“遍地开花”,或许只剩一个月寿命,建议出院回家。
陶远舟的第一反应是,这不可能。半个月前的母亲,虽然由于肿瘤压迫肺部而时有咳嗽,但外表根本与常人无异,在他看来,至少还能撑好几年。他甚至期待母亲能熬到他学成归来,看一眼他未来志得意满的模样……怎么会突然就“只剩一个月”了呢?
或许是受到悲恸与绝望情绪的支配,那天,父子二人在电话两端都非常冲动,最终演变成异常激烈的争吵。
陶父埋怨儿子不肯像其他人一样老老实实工作,非要做留学这种不切实际的美梦,现在家庭情况惨淡至此,他要求儿子放弃留学和摄影,安心留在国内,去找本专业的工作或是考公务员。
尽管明白经济条件的不乐观,尽管对家庭满怀内疚,陶远舟却仍不甘心:他为了留学,拼命学习了三年,为了从事摄影付出种种努力,难道只能在最后关头付诸东流?更何况,他不过是想要摆脱平庸,不过是渴望卓越,渴望实现理想,难道是错的吗?
电话最后,在陶远舟带着哭腔的辩驳中,陶父缓缓开口:“你也知道,我们家的条件非常普通。虽然平时温饱不愁,但是经不起一点风浪和折腾。人要有理想,更要看得清现实,你爸妈只有这个能力,你也要好自为之。”
在广州的住院时,病房窗外的风景
4、“人命算什么呢?”
八月中旬的一天清晨,陶远舟匆匆乘上了开回老家的列车,一小时前,父亲在电话里告诉他,母亲在昨夜突然失踪,让他即刻返回。他们没有多谈,心里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次日上午,陶母的尸体从离家两公里外的小河中被打捞出来,等陶远舟下午赶到时,尸体已经被冻在殡仪馆里等待火化了。
没赶上看母亲最后一眼,陶远舟甚至在心里松了口气,这样他就不必见到被河水浸泡得肿胀变形的母亲,而是一直记得最后一次见她时,那虽然虚弱疲惫,却依然亲切和善的面容。可惜,他当时并不能意识到,这就是母子二人此生最后的见面。
恍惚中,陶远舟想起一件事。某天在公交车上,母亲曾望着车窗外一群嬉笑打闹的年轻人,毫无预兆地问了一句:“假如我没有生病,你现在留学的事该进展到哪一步了?”他没有多想,诚实答道:“应该早就交完了材料,运气好的话签证都拿到了吧。”
此时想起,他从未如此痛恨自己的迟钝和残忍。
葬礼一共举行了三天。最后一天的傍晚,当一切终于告一段落,陶远舟却害怕回到那个空荡了许多的家,更害怕看见摆放在客厅最显眼处的母亲的遗像。
母亲火化那天,他第一次看见尸体被推进炉子里烧,烧完出来变成了一堆灰,还有几块稍大一点没烧干净的骨头。等到要装进骨灰盒的时候,那几块骨头放不进去,旁边的工作人员拿起一把小铲子,开始一点一点敲,直到将骨头全部敲碎,再铲进盒里。
看见工作人员敲骨头的样子,不知怎么的,陶远舟突然觉得特别好笑,拼命忍都忍不住。“人命算什么呢,这么踏实的一具肉体,一会儿的功夫就能烧成灰。不管是多重要的亲人,花了多少钱也救不回来的人,烧完就剩下这样几块顽固不化的小骨头,还要被人拿铲子敲来敲去,真滑稽。”
为了不笑出声来,他只能狠狠掐住自己的大腿。
2018年2月,是申请春季出国的留学生们签证下发的时间,陶远舟几乎整个春节期间都在心神不宁地等待着。然而眼看留学群里的朋友一个个收到了签证,属于他的喜讯却一直没有传来。
春节过后的一天,父亲忽然告诉他,自己当天正在高速上开车时,接到过一个日本来的电话,声称是入管局,要向他了解家庭成员和收入情况。由于上交材料时,陶母尚在人世,并作为经济担保人之一被记录在申请材料中,被问及近况,耿直的陶父在电话里如实交代了其去世的消息,随后,对方就以不妨碍他驾驶为由,匆忙挂下了电话。又过了几天,心中已有预感的陶远舟果然收到了自己被拒签的通知,理由是:经济能力存疑。
5、承担不起的代价
留学的计划搁浅了,但将摄影作为职业的意愿已在陶远舟心中生根,他再也无法割舍。为了能踏上职业摄影师之路,他在父亲的建议下,报名了北京一家民间摄影培训学校。
带着家庭此时全部的积蓄,陶远舟只身前往北京,然而等待他的生活却远不如宣传广告中描绘的那样美好。落后的教学理念和恶劣的住宿环境令他度日如年。六人间的宿舍里,24岁的他是最年长的,其他室友几乎都是中学毕业后抱着“学门技术混饭吃”的心态,被家人送来此处的年轻男孩。宿舍里一片狼藉,每晚响起的游戏声总是让他想起刚上大学时的焦躁。
熬过了花销巨大但收获甚微的半年,终于从培训学校结业的陶远舟在北京找到工作,成为了房产交易平台的摄影师,但紧接着就被分配去了附近省份的一处小县城。
在北京的摄影培训学校
在和老家环境相似的县城里工作了近一年,日子缓慢而平静,甚至有了些“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意思,但越是安稳,他越是发觉,自己心里始终有一处深不见底的黑洞,藏着无言的呐喊与迷茫,怎样都填不满。
就在这个时候,陶远舟意外接到了一个自称是留学中介的电话,电话里的人问他:“现在还有留学意向吗?如果还想再申请,我们可以帮你。”
他没有回答。当初被拒签时,他曾跑遍了市面上几乎所有知名度高的留学机构,询问重新申请的可行性,但得到的答案总是只能令他失望。现在听见了不一样的说法,他心中充满了怀疑,担心对方只是为了那几万块中介费,但比怀疑更真切的心情,是期待。
2019年夏天,陶远舟亲自前往那家留学中介,在现场做了更详细的咨询,在判断过对方所言确有可行性后,陶远舟对留学的执着再次被点燃了。他开始比上次更加积极而谨慎地准备申请材料,并将出国计划定在2020年4月。此时,陶远舟家的经济状况已有较为明显的改善,父亲重新投入工作,陶远舟自己也拿着每月过万的工资,不需要像上次那样四处借钱才能勉强凑够留学保证金。因此,他和留学中介都十分乐观地相信,这次的申请是很有可能通过的。
然而,2020年初,无数人度过了迄今为止最特殊的春天,有许多人的生命轨迹都因为这场疫情而被迫发生改变。
春节过后不久,被困在老家等待复工的陶远舟收到了自己被再次拒签的消息,理由是“对上次拒签理由的解释不充分”,以及和上次一样的,对经济能力的质疑。然而留学中介坚持认为,这不过是表面的理由,实际上是在疫情的影响下,日本对留学签证的审查变得极其严苛,因此劝他“明年再去申请试试”。面对着这样的鼓励和劝慰,陶远舟已没有气力再回复消息。
陶远舟心里比任何时候都清楚,自己再没有勇气和资本去申请第三次留学,也不愿再守着一个支离破碎的梦狼狈挣扎。漫长的准备过程耗费了太多积蓄,更耗费了他本可以用来一心一意奋斗的宝贵时光。
留学,曾一度让他产生踮起脚向上跳就能触碰到的错觉,但他现在懂了,人生其实远不是一次或两次竭力起跳就可以成就的。当风险和意外像风暴一样毫无预兆地袭来,唯有土地足够坚实,才能承托跌落的双脚。他真正缺少的,远比想象中更多。
那个曾经在母亲病重家庭困难时都没能断绝的念想,现在他终于要放弃了。
他使用无人机拍摄的,曾工作过的北方县城
6、回到老家的我们
2020年3月下旬,新冠肺炎的阴影还尚未完全淡去,在恢复营业不久的烤肉店里,26岁的陶远舟坐在我对面,我们以一餐酒肉庆祝疫情之下“家里蹲生活”的结束。
“这顿我请,”我抢先说,“就当是欢迎你,终于回了家。”半个月前,他辞去了在北方的摄影工作,决定回到南方的老家发展,如今刚刚入职一家古玩商行。
比起从前那些日子,为留学做准备而不得不悬着一颗心前进,为多挣点钱而每天加班到凌晨两点,陶远舟如今的生活看似轻松安逸得多。但在我看来,他却并没有因此而过得更开心一些。
他突兀地提起了自己在北方县城工作时的一个黄昏。那天在下班路上,他经过一个卖烤红薯的小推车,瞥见一个穿深棕色长外套的中年妇女。那个人有着细瘦的身形,一头刚开始泛白的短发,走路轻微摇晃,与他记忆中的母亲几乎重叠在一起。
陶远舟停下脚步,看见她上前询问红薯的价格,可一听说要“十块钱一个”,她顿时像一只受惊的小兽那样,不自觉地将身体后仰,往后退了两步,随即露出非常泄气的样子,很快就转身离去。
那一刻,陶远舟的心上似乎重重地挨了一拳,好久都没有缓过神来。
我没有告诉陶远舟,其实我读大学时,也曾向往去海外留学,但我的家庭条件甚至还不如他,因此从未抱有期待,只是凭着兴趣去旁听过日语专业的课,才掌握了一定程度的日语。没想到,后来学校举行了不限专业报名的赴日交换生考试,更没想到的是,并非专业生的我竟能考进前几名,得到了减免学费和住宿费的名额,于是“捡来”一年珍贵的留学回忆。
归国前夕,日方学校曾问我和其他几个留学生,有没有留下读研的意愿,好几个同学开心地选择了留下,而我在与家人视频讨论此事时,见到的是他们为接下来的花费而担忧的愁容。
视频的最后,母亲犹豫着说:“要不,就把咱们家的房子卖了吧。”
想到父母忙碌半生才买了房,连贷款都没还完,负罪感一下击中了我,于是我再没有提过留学这件事,回国就参加了工作。那时,我还曾屏蔽过所有留日校友的朋友圈,因为每当看见他们意气风发,满脸阳光的样子,我都无法抑制从心底汹涌而出的羡慕。
“能够实现理想的人,一定都付出了相当的努力。”我的内心总是响起这样的声音,“但还有更多的人,难道不是连努力的资格都没有吗?”
陶远舟举起手中的啤酒同我碰杯。玻璃相撞,发出一声脆响,他忽然轻轻地笑了,说:“原来,这就是北岛写的: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我不知该怎样回他,只能端起酒杯,猛地灌下一口。






 微信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